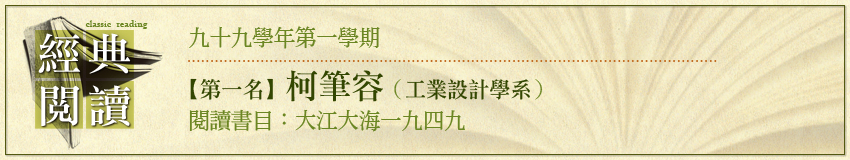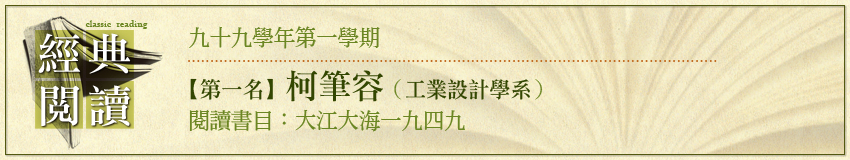人的生命是一首樂章,因為經歷而譜出最獨特的音符。有些樂章只聽見小小的起伏,他們的一生平淡無奇;有些樂章澎湃洶湧,他們的一生精彩輝煌,而在龍應台筆下那遙遠的一九四九,我似乎聽見了那些年代最哀傷的樂曲,樂曲的五線用同袍與敵人的鮮血延續,槍聲與砲聲打出了音符,穿插在其中無數的別離與傷痛譜出了動盪漂離的一九四九。
在二十世紀末出生的我們,從長輩口中與歷史課上知道一群在一九四九年來自大陸的人們,他們踏上了下一代的我們所出生的台灣,他們是
「外省人」。
老一輩的人們對於外省人沒什麼好感,我問為什麼?你就不知道蔣中正來了就統治台灣啦!我們本省人多麼不自在。我點點頭,卻體會不到長輩的不滿。有人說歷史的恩怨會隨著時間而沖淡,我想恩怨就是在傳承中被沖淡的吧!外省人對於長輩們是具象的衝擊,但到了我們,只剩下看不清的輪廓,甚至成了最單純的名詞。
龍應台為我們,為這些在和平中長大的青年,再次畫上那些快消失在歷史洪流中的輪廓,但那不再是區分外省人本省人的線條,而是用最簡單最樸實的線織出在戰爭中最撼動我們靈魂的故事。我們的心,回到了那一年,孩子離開父母,孩子進了國軍,走入十萬大山到了越南,被共軍逼上了台灣,孩子被共軍抓到反過來打國軍,他們別離,在家鄉、在車站,在海港,在戰場,在那一年烽火連綿的中國,這些別離成了他們永遠的痛;永遠的遺憾。
書中為不足道小小的故事都字字牽引著我,文字成了投影片,開始在心中快速的播放,我開始跟著書中的主角起跑。我跟著美君跑到了衡山車站,跑上張玉法搭的往台灣的船隻。一轉身,我看見亞弦頭也不回的與母親訣別。我又跟著豫衡中學的學生在十萬大山中躲避槍林彈雨。我停在香港的調景嶺,看著陳保善的背影,我想告訴他,你懷抱的想要奉獻給國家的熱情,我看見了。我跟著所有的人走了一遭,這一走,我看見了一九四九年的中國。
時間並沒有停在一九四九,故事竟繼續的往前推,推到了德國,推到了太平洋戰爭,時間拉長到整個二十世紀初。這令我們難以想像,就在半個世紀前,人們被戰爭的恐懼籠罩,歐洲的大地被鮮血覆蓋,太平洋因砲火而沸騰,世界因戰爭而撼動。戰火是脫韁的野馬,無論是什們國家,無論是甚麼種族,遇上這匹野馬就是被蹂躪踐踏。
第二次大戰,德國與日本成了戰敗國,同盟國成為世界的勝利者。國共內戰,共產黨將國民黨逼到了台灣,你說,同盟國和共產黨勝利了嗎?多少美國青年的身軀躺在冰冷的太平洋底,多少的「中國人」曝屍在千山萬水中,〈大江大海〉的開頭這樣問,戰爭,有「勝利者」嗎?戰爭帶來太多的不公平,帶來千千萬萬的別離,這些哀傷超越了種族,跨越了時代,他為所有所有的人類帶來絕望。
老一輩談論的一群自大陸來的人們,在我眼中不是外省人,戰爭中獲勝的一方也不是勝利者,世界上所有經歷烽火的人們都是戰爭下的受害者,我為他們在時代中遭遇的不公平流淚。沒有永遠的戰爭,沒有永遠的傷痛,所有走過這段歷史的人們終將默默退出時間的舞台,但他們的際遇,他們的傷痛,不能被世代所遺忘,因為他們用血淚、漂泊與一輩子的悔恨,教導和警惕千千萬萬在和平中成長的我們。
我向這些人們深深的鞠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