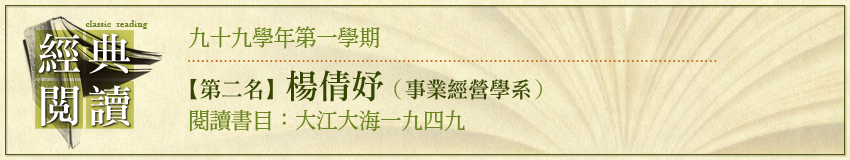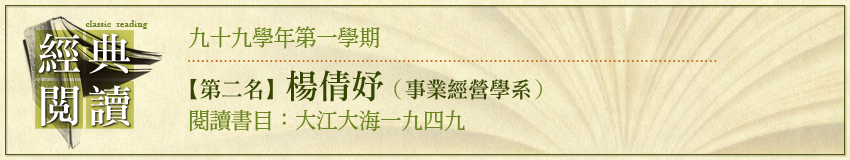一切的恩怨情仇、生離死別都從這裡開始。這是一個顛沛流離的時代,沒有人知道前方是誰在等著他,也沒有人知道自己下一步會在何方,更沒有人知道自己將會被命運帶往哪個方向。時代迫使人們抉擇,抉擇了一個他們無法控制的時代。
一九四九,一個烽火連天的年代,侵略與被侵略同時在這個舞台上演著,誰是受害者、誰是迫害者都沒有一個公平的準則,有人被迫離開家園,有人被迫手染鮮紅,有人被迫失去了自我,他們全都是大時代的受害者、宿命的犧牲者。
美君,作者龍應台的母親,在她的生命裡總是有一條壯闊清澈的新安江,那是她印象中的故鄉。可惜她的故鄉撐不過大時代的風雨,數十年的光景,山河劇變,再回首,原以為不會動搖的故鄉沉入湖底,從地圖上消失。懷生,美君的夫婿,一口濃厚的湖南腔,從小在龍家院成長。時代像一把斧頭,劈開了他的世界,一邊是她的母親,一邊是不完整的他,從此他只能隔著海峽遙望那來不及告別的母親。那個年頭,人們四處流竄,每一個港口都上演著離別的戲碼,帶著不安與恐懼辭別自己的至親和熟悉的家鄉,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能再聚首,也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能再回到這片土地,是戰爭結束後?是世界和平時?還是永遠都無法回到最初的原點?
那是一個回不去的時代。嘶吼、淚水、傷痕以及一顆顆千瘡百孔的心,是戰爭帶來的見面禮。戰爭是何其殘酷,它所畫下的傷口是永不結痂的創傷,至今依然在淌血;它逼迫一個人奪取他人的生命來保護自己。戰場上有些人讓自己身上沾滿別人的鮮血,有些人則寧可人頭落地也不願向敵人低頭。是什麼樣的戰爭思想能讓人如此乖戾殘暴;又是什麼樣的信念能使人不向生命低頭?許多人小小年紀就被送上戰場,他們還無法判斷是非對錯,就只能盲從長官、軍法。連碗筷都拿不好的年紀,被逼著批上戰袍、被迫持槍殺人,沒有人能解釋這種看似光怪陸離的現象,蔣介石、毛澤東、日本天皇都無法給一個令人心服的解釋。張玉法先生和他的二哥在戰場上分道揚鑣,一個往北、一個往南,投身不同的軍營,國軍、共軍對他們來說並沒有差別。這是一場賭注,無論戰爭輸贏都有傷亡的可能,但是這是唯一可以延續家庭命脈的希望。李維恂,八百壯士和拉包爾戰俘營的倖存者,他對作者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在等這個電話。」他在等一個能夠清洗傷口的機會,打開他心中的「黑盒子」。時代的漩渦將他們的世界狠狠的捲了進去,漂泊異鄉的身、心、靈何時才能得到救贖呢?
那個年代有許多台灣的「皇民」被送往南洋作戰,他們為別人打仗,打了一場錯誤的仗,他們是「台籍日本兵」。他們被日本人壓迫、被中國人憎恨,卻從來都沒有一個他們能夠發聲的立場。沒有人願意打這場仗,戰爭只不過是醜惡的權力鬥爭。我的祖父也曾在二次大戰期間被派往印尼沙巴、沙勞越一帶,幸運的是,他是後勤的通譯官,不用在第一線染上鮮血。那時他十九歲,年少瘦弱的他曾一肩擔負一千多名當地居民的生命。因為當地不識字的居民收集了美軍的文宣傳單,惹惱了日本軍官,在祖父極力的勸說之下,挽回了一千多條寶貴的生命。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運,許多人還來不及認識生命,就已經被迫接受死亡。
對於命運,人們總是充滿了不確定性,人生旅途總是出現分岔路。命運的大潮流將人們沖刷至各地,散落異鄉,卻從來都不曾給過一個完整的結局。沒有人能夠對他們的時代負責,沒有人能夠做一個客觀的解釋,連他們自己也無法定義這個荒唐、悲涼的年代。台灣這片土地上住著各種不同背景的族群,卻有著相同的傷口──隱忍不言的傷。有誰能幫他們找回充滿歡笑的年華歲月;有誰能替他們解釋那個荒唐的從前;又有誰能為他們拼湊一個完整的人生?戰爭已經落幕,但和平的鐘聲似乎尚未敲響,太多的因素造成他們對彼此的不諒解,仇視、敵對、猜忌造就了嚴重的省籍衝突。明明都是台灣人,卻無法包容在異鄉文化成長的彼此。時代的劍斬斷了人與人的信任與包容,加深了人與人之間的隔閡。
我常省思,祖父母與父母的年代要過的多麼艱辛、坎坷,才能換給我們一個平靜的世代?在大人的眼中我還是個十九歲的半大人、小孩子,這是一個尷尬的年紀,作者卻希望他那和我同年的兒子能夠知道那個我們不能理解的六十年前。我們要試著認識我們沒有經歷過的時代,並記取歷史的教訓,從歷史中學習。我們生長在什麼時代之後,又將創造什麼樣的時代?時代會造成許多變遷,從具體的事物到抽象的情感都有可能受到歲月的磨練,但一切的風起雲湧、顛沛流離最終都將流入「大江大海」,而將海上載浮載沉的就是我們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