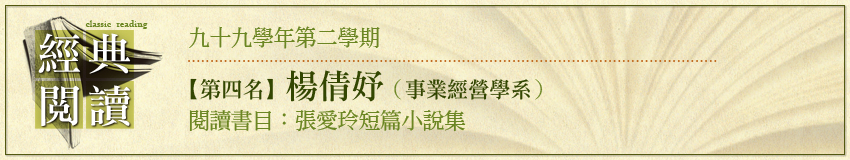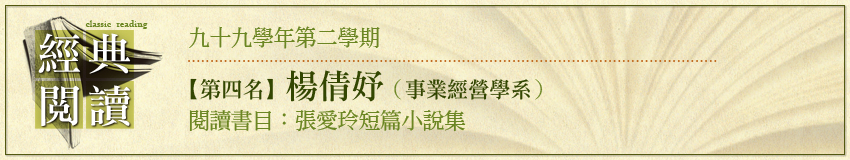翻開張愛玲的小說,一字一句皆是七情六慾的真實寫照,彷彿不用天馬行空的幻化出虛構的情結,就能將身邊的現實體悟都堆砌成刻骨銘心的文字。她的文字在真實與可悲的雙軌上並行著。真實的是,她以說故事的口吻,將人物的情感以平淡的文字做敘述;可悲的是,那看似輕描淡寫的情感是充滿情慾的烈酒,燒得無法入喉,更抵不住它悲愴的後勁。
這種令人感到強烈的無奈來自於張愛玲不快樂的童年:父母的離異、繼母的欺侮、父親的墮落於沉迷,全都縮影成張愛玲筆下的世界。有別於中華文化的傳統思想,她的作品鮮少有快樂團圓的大結局。張愛玲從小就閱讀《紅樓夢》──打破中國傳統團圓結局的第一作,故事中人物們的鉤心鬥角、機關算盡、情感宿命,無形中成為她在處理故事情節時的一大推手,她總會細膩強調人物內心情感糾葛,刻畫出人性情慾的黑暗面。
「情感」是張愛玲的小說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濃烈的、平淡的,親情、愛情、仇恨,用不同組合譜出一篇篇的文字。張愛玲出生於因戰亂而動盪不安的民國初年,滿街上充斥著中國人尚未完全消化的「洋味」,女權意識也隨之逐漸抬頭。但是在這個過度期,女性的思想依然受制於父權社會,處處備受打壓,而張愛玲的小說人物也承載了這種風氣,無論是男人或是女人皆有扭曲的不完美性格。就因為她的人物不是光鮮亮麗的完人,才能讓讀者感到一抹揪心的空虛與無奈的惆悵。完美的不真實,而真實的就是拼圖中永遠缺少的那一塊,人們在追尋「完整」的過程中,常常發生擠壓、摩差、碰撞,我們在他人身上找尋我們自己本身所缺乏的,而別人亦在我們身上索取他們所需的,藉此得到彼此心靈上的慰藉。
張愛玲的小說常常藉由軟弱帶著缺陷的主角諷刺人生百態的無奇不有,她筆鋒下的文字常常是沒有希望的,故事的開始就已經註定了結局的荒誕與悲涼。人性的黑暗面在她的文字中表露的一覽無遺,描寫人心因為情慾而扭曲變形。〈第一香爐〉中的梁太太為了滿足自己荒唐的私慾,不惜將自己的侄女扮成交際花很狠的推入火坑。然而因為環境的誘惑與逼迫,葛薇龍自嘲是自願作賤的,犧牲,不過是美化了她自甘墮落的藉口。打趣的是,這篇故事開端的霉綠斑斕的銅香爐與沉香屑,已經預告了這齣鬧劇的結局。
在張愛玲的小說世界中,人與人的情感關係是錯縱複雜的。〈茉莉香片〉中的聶傳慶因缺乏親情,而養成了一種詭譎的性格。他認為母親二十年前的抉擇是牽絆住他一生的累贅,並對自己母親的初戀情人有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對他而言,父親聶介臣是無法擺脫的可笑存在,在午夜夢迴間都不想面對的宿命;而言子夜是他逃避現實的窗口,他不斷的幻想:若我的父親是言子夜,我的人生一定會有不同的轉變。然而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終究讓他的心魔啃蝕他的理智,莫名奇妙的妒忌著無辜的言丹朱,甚至讓這把無名的妒火燒毀了自己的世界。人格的扭曲源自於對愛的渴望,可悲的是他親手把關愛推入深淵。
〈紅玫瑰與白玫瑰〉是典型的二元論,非黑即白,只有正與反兩種選擇。她將兩個性格迥然不同的女子塑造成兩種鮮明的對比,「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成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飯粘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永遠都是得不到的最好,不能緊握在手心的才會驅使人們去追求,然而在汲汲營營的尋覓之下,人們就錯失了屬於自己的選擇權。張愛玲將佟振保的表面塑造成好人的形象,並賦予他選擇的權力,然而他才是被人性情感所抉擇的選項。
張愛玲的小說顛覆許多人對情感小說的認知,猶如一口飲下愛恨情仇所釀造的酒一般,在喉嚨燃燒的是人們不願面對的真相。張愛玲將最真實、最不堪的人性面呈現在我們的面前,把一切存在已久的細節放大,檢視後才發現,人們沒有控制情慾的力量,我們充其量就只是被情感所支配的木偶,活在虛幻飄渺又荒唐的紅塵。
|